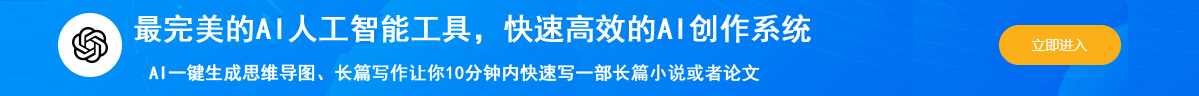当172公分、55公斤、26岁的前建筑公司职员秋雨走进江苏镇江一家小型直播公会直播间时,她穿着一件紧身圆领长袖,领口到锁骨。这是她在一家头部直播平台作为“颜值主播”开播的第一天,公会运营告诉她,“26岁”恐怕不行,因为“大哥”们(平台愿意持续打赏的观众)喜欢更年轻的,这件衣服也不行,“太臃肿”,要换掉。“所以在直播间我只能说自己22岁,我的几个同事是单身妈妈,她们会说自己是98年、96年的,比实际年龄小5岁。”2024年12月,秋雨坐在用做主播半年挣到的蔚来汽车里对我说。
第二天她换了一件圆领紧身短袖,领口在锁骨附近,运营还是不满意。“他先说衣服颜色不好看,然后让我去看公会里别的女主播是怎么穿的。”秋雨说,直播间的门都是打开的,她一一走过,每一间都是吊带或者超低胸紧身T恤,“领口过低,就往露出乳沟的地方垫一张餐巾纸”。
后来她从其他主播那里听说,垫餐巾纸一是为逃过平台审核(衣领太低可能被判定为违反平台规则),二是能让观众的目光聚焦在餐巾纸所在的地方,引发遐想。秋雨说,公会不会特地说明着装的边界是什么(这个新世界的规则需要她自己揣摩),只会在合同里列出打赏的钱怎么分:五成归平台,两成归公会,三成归主播。主播每周工作6天,每天播6小时,底薪5000块。
“没有门槛,(入职前)唯一一个需求就是加你微信看看你朋友圈的照片(长得)别太离谱。”秋雨说。
2022年11月,苏州大学博士生潘莹入职当地一家只有2名运营的小型公会,成为一名秀场主播。这一个月是她博士论文田野调查的重要部分。访谈过超过20名秀场女主播、11家公会运营后,她告诉我,女主播们真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,公会运营会帮每个女孩调好属于自己的美颜滤镜。
“前面运营本来都不想要,然后我说我试试,看看能不能调。”成都一家公会的24岁男运营知山对自己的调滤镜技术十分自信,向我展示一个来应聘女孩调前调后的对比照。他把这组照片发了朋友圈,配文“你们现在还相信抖音有美女吗?”知山告诉我,调滤镜的运营“基本都是男生”,因为“男人才了解男人”。他管理超过10名直播平台娱乐主播,全公会有1000名左右在线主播。
潘莹说,这行里金主“大哥”多、打赏金额高的女主播被视作标杆,所有人都得向她们看齐。公会运营会要求旗下主播“多看多学”,女主播们会复制“标杆”的穿着打扮、动作姿态、语言形式。久而久之,女孩们的形象统一成了一种模板,“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”。她向我描述一个新人用来学习的“典范”视频,“(那位标杆主播)胸部非常夸张,每天晚上不停地跳热舞,声音非常夹子”。还有一些更细节的知识点,比如潘莹的同事小雪“学习”到在镜头前穿有破洞(而不是全新的)的黑色丝袜更受“大哥”欢迎,“可能(男性)会幻想把丝袜撕掉”。

入职没到一周,公会运营第三次暗示秋雨着装“不对劲”。她被带到另一个直播间,要求现场向这里的同事们学习穿衣。这里身着吊带和“护士服”的性感女孩们指出,秋雨的紧身T恤“太老土了”,解决方法很简单,去购物网站搜“主播上镜服”。“(她们说)二三十块钱一件,不贵,(让我)买几件来回穿。”秋雨说。
秋雨按女孩们给的关键词搜索,大胸细腰的模特图(其中一些衣领开到胸部以下)填满了屏幕,商品名都带有“纯欲”“性感”字眼。搜索一次后,购物网站开始自动向她推送情趣内衣、“水手服”“护士服”和“性感丝袜”,搜索框建议她检索“娱乐主播服装有心机”——算法似乎比秋雨更懂她需要穿什么,她一口气下单了近三十件畅销上镜服,包括“包臀紧身裙”“护士服”“紧身旗袍”等等,“吊带抹胸居多”,“(全都)勒得特别紧”。
换上新衣服,其他女主播开始夸她“好看”“上镜”,运营也再没有让她去“学习”了。“我意识到这一天还是来了,本来想能推迟一天是一天。”秋雨说。

运营负责包装主播,首先是灯光、滤镜、衣着,然后是表情、动作、语言。
穿着过关后,运营告诉秋雨,短视频也是很重要的个人形象展示环节,被称为“流量入口”:如果观众喜欢短视频,就更可能点进直播间,才会有后续打赏行为。他建议秋雨,从下往上拍自己的大腿,然后让腿上的肉抖起来,因为“大哥特别喜欢这样的画面”。秋雨不想拍这些视频,为了让账号上有内容发布,她会下载那些购物网站推送的情趣内衣照片,用修图软件把模特的脸换成自己的交差。
“公会说几点发(短视频)就几点发,让我们拍什么风格我们就得拍什么风格,天天发,粉丝涨得也挺快的。”主播颖儿在接受潘莹访谈时说。潘莹没拍,她在网上下载那些“更撩的”视频,通过AI换脸生成自己的短视频。
“二十多岁的女孩们往往还没经历社会历练,很容易被公会的思路影响。”32岁的主播洺瑜告诉我。她2017年入行,见多了年轻女孩想挣快钱,结果往往三个月都坚持不了。在她看来,能坚持下来最重要的是想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干一行——这行只适合现实主义者,或者说,那些承担着“房贷怎么办,车贷怎么办,家庭开支怎么办”的人。
疫情时期,洺瑜全家人“连米都拿不到”,她靠一个月25000元的打赏交上了电费、买到了菜。“外面风大雨大,只要你有电,你有网,你就能开播。”洺瑜说。
秋雨的公会规格很小,只有十多个直播单间(多数时间坐不满主播)和3名运营,但全职HR就有3人,负责不停地招女主播。这些小公会的HR们成了各大app上唯一对秋雨“主动出击”的招聘人员。

和同事们熟悉后,秋雨发现和直播间中表现出的轻松甚至轻佻相反,女主播们的线下生活一个比一个沉重。有人是因为老公欠了巨款要帮着还钱,有人是单亲妈妈要独自养家(这位单亲妈妈提到她读小学五年级的儿子曾突然闯进直播间,吓得她慌忙说了句“有点事”就下播了)。一次聚餐时,同事“十五”边说着家里的情况边放声大哭,她丈夫因为涉赌入狱,为了不连累她要跟她离婚,但她决定不离,做主播养活四岁的孩子,等待丈夫出狱的那天。
前“厂妹”颖儿告诉潘莹,她的男朋友退伍回来后很穷,没有工作,她自己初中二年级就辍学,只能做餐厅服务员或厂妹,她不想再吃苦,所以一直在做女主播,换了好几个平台。和颖儿一样,潘莹接触的多数主播出身“厂妹”,她们公会所在城市密集分布着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,疫情后许多女工加入直播公会,暂时缓解了就业焦虑。
“近些年该地区涌现许多中小型直播公会,在昆山、太仓还出现了泛娱乐的‘直播小镇’。”潘莹在论文中总结道,这些“涌现”和传统制造业的地理布局密切相关。

潘莹入职的M公会成立于2022年6月,管理层由4人组成:老板,过去职业是挖掘机包工头;老板娘,曾是“酷狗”平台女主播,老板是她过去直播时的榜一大哥;运营张凯,曾是KTV领班,和老板是老乡;运营周涛,曾是快递公司货车司机,后来跟着老板开挖掘机,他有一家老小,开车卖力,困得受不了会喝风油精提神。截至2023年9月,M公会共有172名主播先后入职,仅留存20名,流动性极大。
主播洺瑜说,“圈外人感觉公会很神秘,其实都是草台班子,公会招运营没有什么要求……即便是王牌运营,出门在外,身份也是靠自己给的。”
公会强调与主播之间是“命运共同体”关系。潘莹做主播期间,经常听到老板娘和运营说“我们是自家人”。女主播们几乎都是前“厂妹”,没地方住,公会提供宿舍,没有直播设备、空间和衣服,公会提供设施完备的直播间。“那些疫情后原来在江浙沪一带电子厂的厂妹们像浮萍一样飘着,直到进入公会,就像获得了暂时的安身之处。”潘莹说。大家产生了一种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、有钱一起挣的江湖义气。公会在一栋写字楼3层,那层只有这一家公司,晚8点女主播们上播时走廊漆黑,门口公会招牌亮得耀眼。招牌下是一处佛龛,供奉着财神爷,香火不断,烟味飘散到二楼直播间。
潘莹对小型公会的“江湖气”印象深刻,公会不止为女主播们提供庇护和便利,也通过严格的考勤制度、罚款措施和言语羞辱等手段进行“洗脑式管控”。
研究者们认为,主播在直播间与观众互动,出售直播间里能售卖的一切,包括氛围、外貌、才艺、社交能力,与观众建立关系,典型的关系是介于朋友与恋人间的“暧昧关系”,因此被称为“暧昧经济”。

洺瑜会提醒女主播们明确自己和观众之间是“买卖”而不是“情感”,实际工作中,两者的边界很模糊——和演员表演一样,长期的情感劳动可能演变成情感本身。颖儿告诉潘莹,直播平台那么多,女主播那么多,但她的大哥就愿意一直停留在她的直播间里刷礼物,这种“就愿意”意味着“产生了感情”。
一个有趣的事实是:学术界分析时,倾向于将主
[免责声明]如需转载请注明原创来源;本站部分文章和图片来源网络编辑,如存在版权问题请发送邮件至398879136@qq.com,我们会在3个工作日内处理。非原创标注的文章,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,不代表炎黄立场。